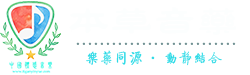拿什么拯救你,我的疼痛?
2018年8月31日,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,一名待产孕妇坠楼身亡。事后,医院发表声明,称家属多次拒绝剖宫产,导致产妇疼痛难忍、情绪失控跳楼;家属则否认这一说法,表示一直同意剖宫产,是医院认为“马上能生”、没有剖宫产的必要。
事情的真相,还有待时间去检验。不过,这已经不是首次发生类似事件了。早在2014年,就有患者因为腹痛难忍、跳楼自杀。[2]
那么,疼痛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疼痛是如何产生的?
2001年,国际疼痛研究学会(IASP)将疼痛定义为:与实际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感觉和情绪体验,或用这类组织损伤的词汇来描述的自觉症状。[3]
这话看上去有点儿绕,我们就打个比方来说明吧。
打电话时,偶尔会出现杂音,这说明外界存在某种电磁波。这种电磁波干扰了手机信号,进而影响到手机对信号的解析,导致话筒出现异常。
疼痛的传导(图片来源:www.hospital-cas.cn)
疼痛也是一样。内在的或外在的不良刺激作用于外周感受器,引起神经冲动,沿着神经通路逐级传导,经脊髓、脑干等中继站中继,最终进入大脑;大脑对这些神经冲动进行解读和整合,人体就会产生痛觉。
体感音乐: 平衡身心灵 让心情好起来 ~
本草音乐(藥)像药物一样有味道!
疼痛咋调节?
当然,人们不会对异常无动于衷。工程师们想出了很多降低噪音的方案。比如,优化信号的传递;比如,增强手机对信号的解读能力;比如,通过分析相关数据,开发出了主动降噪技术……
20世纪60年代,英国生理学家P.D.Wall和加拿大心理学家R. Melzack提出了疼痛的“闸门控制学说”,认为人体内,也有一个信号优化系统。[4]脊髓既接受外周感受器的信号,又接受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,两相叠加之下,只有不良刺激的强度超出人体的调节能力时,才会出现疼痛。
闸门控制学说(图片来源:netclass.csu.edu.cn)
随后,70年代,学者们又在脑内找到了阿片受体,并因此认识了下行抑制系统。下行抑制系统是中枢神经系统疼痛调节的一部分,其功能跟手机的主动降噪相似。[3]例如,临床上常用的阿片类镇痛药,就能激活人体的下行抑制系统,弱化、抑制甚至阻止外周传来的痛觉信号,产生镇痛效果。[5]
吗啡,最常见的镇痛剂(图片来源:www.bioon.com)
产痛,这种疼痛很特别……
说了这么多,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:产痛,非常特殊……
产痛的特殊性,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个是疼痛机制,一个是疼痛级别。
前面我们提到,疼痛是由不良刺激引起的;而产痛的定位,却很含糊——只要生孩子,就必然出现产痛,这到底算不算不良刺激呢?
产痛(图片来源:www.tiganyinyue.com)
分娩的过程,包括三个阶段,也就是常说的三个产程。第一产程,从子宫收缩开始,到子宫颈口完全张开为止,伴随着胎头下降和胎膜破裂;第二产程,始自子宫颈口全张,延续至胎儿产出,子宫收缩短暂停止,然后重新出现,且较第一产程更为强烈,每次持续1分钟或更长,间歇1到2分钟,电影电视里常出现的“屏气”、“用力”,就发生在这一阶段;第三产程,不像前面两个那样绵延数小时,通常只需要10到30分钟,主要任务是娩出胎盘。[6]
通常说的产痛,来源于子宫收缩,随着子宫收缩的力度增大而逐渐加剧。因为子宫收缩有短暂的停顿,所以产痛也是断续的。在范围上,产痛以下腹为中心,可以牵连到腰骶、盆腔和大腿;在形态上,因人而异,多数是痉挛性疼痛。
此外,有些产妇的产痛集中在腰骶部,称之为腰痛性分娩。腰痛性分娩是由胎位不正导致的,所以,和正常产痛不一样,不会间歇,而是一直持续。[7]
分娩镇痛不完全总结(作者制作)
关于产痛,网络上众说纷纭。最常见的说法是,“人体最多只能承受45单位的疼痛,而产痛高达57单位,相当于20根骨头同时骨折”……

VAS评分(图片来源于网络)
其实,不管是产痛还是一般疼痛,都非常主观,目前尚没有很好的测量办法。临床上常用的视觉模拟评分法(VAS),是由Hayes发明的。在纸上画一条10厘米的横线,一端为0,表示完全不痛;一端为10,表示无法忍受的剧痛。测试时,让患者根据自身的感受和疼痛的强度,在线上做出记号。[8]一般数字大于3,就建议采取干预措施。
谁来拯救分娩疼痛?
当然喽,不管怎么测量、如何描述,产痛都属于剧痛级别。既然会出现剧烈疼痛,那就必须妥善应对。
分娩镇痛可以分为两种,分别对应疼痛调节的两种机制。
首先,根据闸门控制学说,中枢系统的状态会影响人体对疼痛的感受。因此,在分娩过程中,丈夫、亲属、医生、护士对产妇的支持和宽慰,可以在一定程度降低产痛。
其次,可以借助下行抑制系统,直接减少疼痛。比如,给产妇注射吗啡类药物。起效快,效果确切,持续时间也较长,但是,这些药物可以通过胎盘进入胎儿,可能会对新生儿产生影响。
所以,更好的方案,是无痛分娩。
无痛分娩示意图(图片来源于本草音乐网)
无痛分娩起源于19世纪末,经过多次技术迭代,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走向成熟。最近半个世纪以来,又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,不断取得突破。[9]
无痛分娩,也就是硬膜外麻醉,首先要在腰背部进行穿刺,将导管穿入患者的硬膜外;接着,用胶带对导管进行固定。整个过程耗时极短,引起的疼痛也很轻微。导管连接着局麻药物,并配有调节阀门,方便产妇根据自身感受,自行控制药物的剂量。而医生,一方面会对产妇进行疼痛评级,评测镇痛的效果;另一方面,会对产妇和胎儿进行连续监测,确保其安全。[7]
无痛分娩,利弊如何?
硬膜外麻醉最大的好处是有效。一方面,国内外的大规模研究都显示,硬膜外麻醉镇痛的效果非常确切;[10,11]另一方面,硬膜外麻醉可以在第一产程就开始使用,最大限度地减少分娩时的痛苦。
也有人批评硬膜外麻醉技术。这些批评通常集中在两个方面。[12]
第一,硬膜外麻醉会不会对产妇产生影响?
答案是不会。
作为一种成熟的、广泛运用的技术,硬膜外麻醉的安全性毋庸置疑。硬膜外麻醉的原理,是阻断子宫的痛觉传导,使其无法进入神经中枢、引起痛觉。因此,硬膜外麻醉中使用的麻醉剂剂量,远小于一般手术中的用量。
据估计,美国每年约有400万产妇,其中,约有160万会选择硬膜外麻醉。[13]其中,出现不良反应的,少之又少;这些不良反应中,多数又是瘙痒、恶心等较为轻微的症状。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女性,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头痛。而这种疼痛,并不致命、且可以缓解。[7,14]
第二,硬膜外麻醉会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?

纠结的孕妇(图片来源于本草音乐网)
一种批评是,硬膜外麻醉会减少子宫的收缩力度、延长产程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……
另一种批评是,硬膜外麻醉会直接影响胎儿,引起胎儿心率下降、影响胎儿正常进食,甚至干扰胎儿的神经功能。
说实话,关于硬膜外麻醉对胎儿的作用,虽然研究很多,但是目前还没有特别确切的结论。Harper在《Gentle birth choices》中提到的硬膜外麻醉会干扰婴儿大脑,进而影响正常哺乳,而另一些研究则显示,硬膜外麻醉既不会影响婴儿的状态,也不会干扰母乳喂养。[15]
所以,不妨换一个角度看问题:2007年到2008年,中国的剖宫产率高达46%,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定下的警戒线(15%),究其原因,主要是社会性因素,比如希望缩短产程、减少痛苦;剖宫产是一种手术,有着较为严格的手术指征和适用范围,盲目追求剖宫产,往往会增加分娩的风险,引起出血、感染、盆腔炎等疾病;而无痛分娩,恰恰可以减少社会性因素引起的剖宫产。[16]
当然,无痛分娩不是万能的。一方面,对于有凝血障碍、全身感染或者不适合自然分娩的人,禁止使用;另一方面,与其他所有患者一样,产妇永远拥有知情权和选择权。
莎士比亚在《李尔王》中写道:“我却被绑在火轮上,甚至我自己的热泪也溶铅似的在烫我。”所有动物都会有不适感,但是,只有人类可以解读、理解他人的痛苦,可以感同身受。所以,普及无痛分娩,势在必行。
影响无痛分娩普及的原因,一是国内麻醉技师人员紧张,无痛分娩至少需要4小时以上的检测,这种工作量,依靠现有的麻醉师,根本没办法承受;二是人们对分娩镇痛知识的缺乏,“生孩子哪有不疼的”等言论不绝于耳。
天然存在的,未必就是合理的。不然的话,还要医生干什么呢?
参考文献
[1] 现代快报. 产妇跳楼双方发声 医院称有监控证女孩跪求剖腹[EB/OL]. (2017-09-05)[2017-09-06]. http://news.sina.com.cn/s/pa/2017-09-05/doc-ifykpysa3452952.shtml.
[2] 【医生们,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?[思考]】据... 来自环球时报 - 微博[EB/OL]. [2017-09-10]. http://weibo.com/1974576991/BbJnGeowR?type=comment#_rnd1505032742911.
[3] 赵欣, 于布为. 疼痛机制研究进展[J]. 上海医学, 2007, 30(6): 462–465.
[4] 韩济生. 疼痛机制研究对疼痛治疗的推动作用[J].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, 2002, 17(1): 8–9.
[5] 杨宝峰. 药理学[M].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8.
[6] 乐杰. 妇产科学[M]. 人民卫生, 2008.
[7] 威廉·卡曼, 凯瑟琳·亚历山大|译者. 你一定要知道的无痛分娩[M]. 胡灵群, 译.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 2010.
[8] 孙兵. 视觉模拟评分法 (VAS)[J].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, 2012, 28(006): 645–645.
[9] SILVA M, HALPERN S H. Epidural analgesia for labor: Current techniques[J]. Local and Regional Anesthesia, 2010, 3: 143–153.
[10] 黄叶莉, 王玚. 无痛分娩的研究进展[J].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: 下旬版, 2006(2): 62–64.
[11] FREEMAN L M等. 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a with remifentanil versus epidural analgesia in labour: randomisedmulticentre equivalence trial[J]. The BMJ, 2015, 350.
[12] HARPER B. Gentle birth choices[M]. Simon and Schuster, 2005.
[13] STARK M A. Exploring Women’s Preferences for Labor Epidural Analgesia[J]. The Journal of Perinatal Education, 2003, 12(2): 16–21.
[14] Using Epidural Anesthesia During Labor: Benefits and Risks[EB/OL]. American Pregnancy Association, 2012-04-26. (2012-04-26)[2017-09-06]. http://americanpregnancy.org/labor-and-birth/epidural/.
[15] ZUPPA A A等. Epidural analgesia, neonatal care and breastfeeding[J]. Italian Journal of Pediatrics, 2014, 40.
[16] 邹惠兰. 无痛分娩在降低社会因素剖宫产率中的作用[J]. 中国当代医药, 2011, 18(4): 34–35.
上一新闻:中医对感官的运用令人们信服
下一新闻:什么是慢性疼痛?